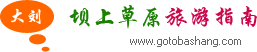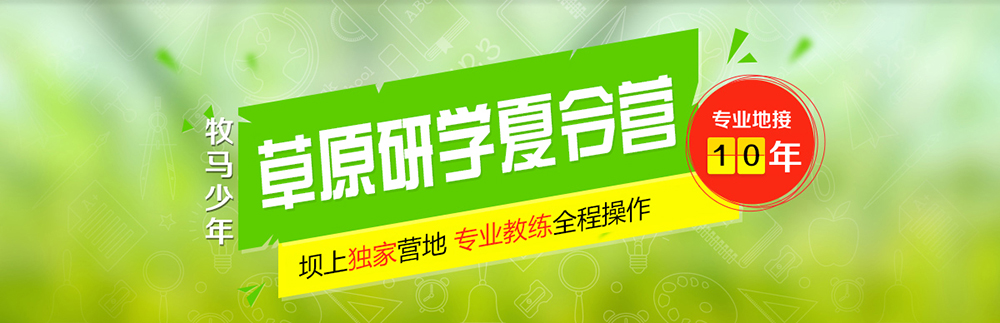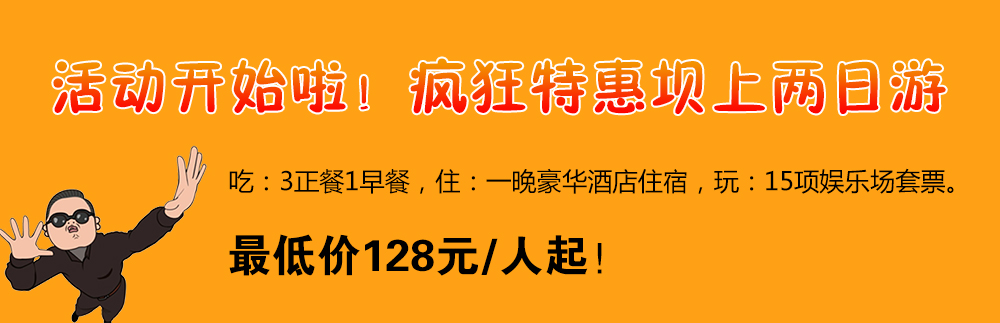沿111國道北行200公里,就到了豐寧壩上草原,這里盛產大豆、莜麥和胡麻油。以此三種東西為原料的莜面苦力,是一道地道的鄉(xiāng)野美食。
壩上農家做苦力,通常都是用大灶鐵鍋,以麥秸為柴。鍋內放胡麻油少許,燒熱、蔥花熗鍋后加入熱水,撒一點食鹽。湯燒沸后放入去皮的土豆燉煮,待土豆酥爛時再徐徐撒入莜面并不停攪動,直到鍋內湯汁基本收干,土豆泥與莜面混成一體為止。接下來蓋上鍋,改用小火燜蒸,在此過程中依舊要經常攪動。及至面中水份蒸去大半,形成松散的顆粒,苦力也就做成了。剛出鍋的苦力,色澤褐黃,油香面香土豆香混合而成的特殊香味直撲鼻孔,入口綿軟爽滑,嚼起來異常筋道。食時若能佐以酸黃菜(壩上人自制的一種小菜,常以芹菜、胡蘿卜絲為原料,色微黃,味咸略酸),味道會更加甘美。
苦力之名我自小就熟悉,《豐寧滿族自治縣志》中也有關于它的記載,但那里面僅僅說它是一種地方食品,名稱的來歷與含義至今無人可考。在過去,這種味美、易做、耐饑的東西曾經在很長時間里供當地貧苦的老百姓充饑裹腹、打牙祭,幫他們度過許多艱難的歲月。到了今天,壩上搞起了旅游,它又成了一道地道的地方風味,不僅讓游人一飽口福,而且也給當地人帶來了經濟效益。
草原食趣
盛夏的壩上草原,鮮花如錦,翠野接天,引得無數游人來此避暑度假,縱馬馳騁。當他們滿意而去時,總流露出一絲意外的驚喜。數年來,我一直為這一絲驚喜所困惑。幾經詢問才知道,他們在草原上吃到了許多新奇的東西,吃出許多情趣來。
七、八月間的草原,一陣小雨過后,茵茵綠草間閃爍起一群“星星”,那是草原上特有的口蘑,白嫩肥厚,采回去清水煮湯,加點兒鹽,湯沸即食,清香嫩滑,未及仔細咀嚼便溜入肚中。更有趣者,攜帶素油、精鹽至野外,燃起一堆篝火,待火焰燃盡只剩下紅紅的炭火時,采口蘑數只,拔去菌柄,菌傘上就升騰起縷縷白氣,油鹽盡滲入褶頁之中,異香撲鼻。取食之,別有一番滋味,食后口齒余香久久不去。草原上有大黃,綠葉紅莖,粗大鮮嫩,采其莖剝皮后上屜蒸熟,加少許白糖食用,酸甜適度,令胃口大張。草原上的淺山丘陵,森林茂密,林間遍生一種野菜,淺綠色,粗莖,莖一側生長著細碎鋸齒狀略顯卷曲的葉子,整株形如鳥翼,其名字叫野雞翅膀子,十分形象。捋上幾把帶回去洗凈切碎,然后備數片肥肉,半鍋清水,煮至肉爛湯肥時加入野菜。開鍋全飲湯、其味美無法以文辭表達┄┄
草原上的飲食,并非僅僅一個“野”字就能概括其面貌,它們往往在野的中間蘊含著一種粗獷豪放的民族精神,烤全羊、手把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壩上的羊只,食鮮嫩的綠草,飲清澈的河水,其肉質鮮嫩,膻味極小。選百斤以內者宰殺剝皮去掉頭蹄內臟,置于專門制作的鐵架子用炭火烘烤,不時翻動并刷上調料。待其外表稍焦時,以刀片一層食之,鮮香異常。片肉的刀法要講究,太薄,僅下一層焦肉,無法體味到外焦里嫩的效果;太厚,割下許多生肉,難以入口。手把肉的取材與烤全羊相同,只是將整羊斬成大塊,清湯白煮,肉略生,手把刀切而食。肉做法不奇,貴在原汁原味,吃法豪放。
草原飲食,頗具草原風情,粗獷中蘊有極豐富的內涵。看上去極普通勞動者的莜面窩子,非一面三熟而不可成:莜麥炒熟,莜面燙熟、窩子蒸熟┄┄如此精工細做之物,怎能不讓游客嘆服,食之又豈有無味無趣之理?